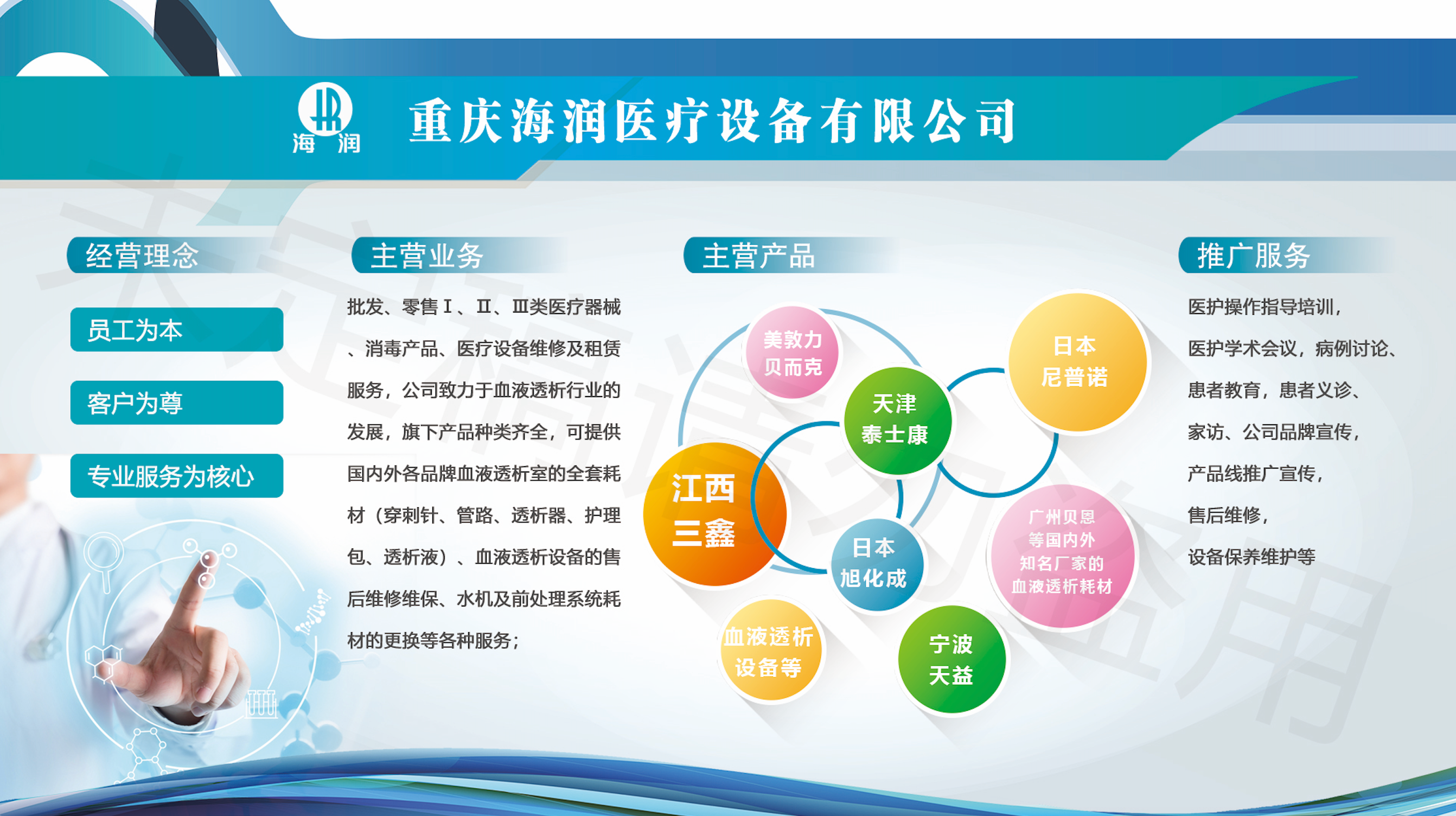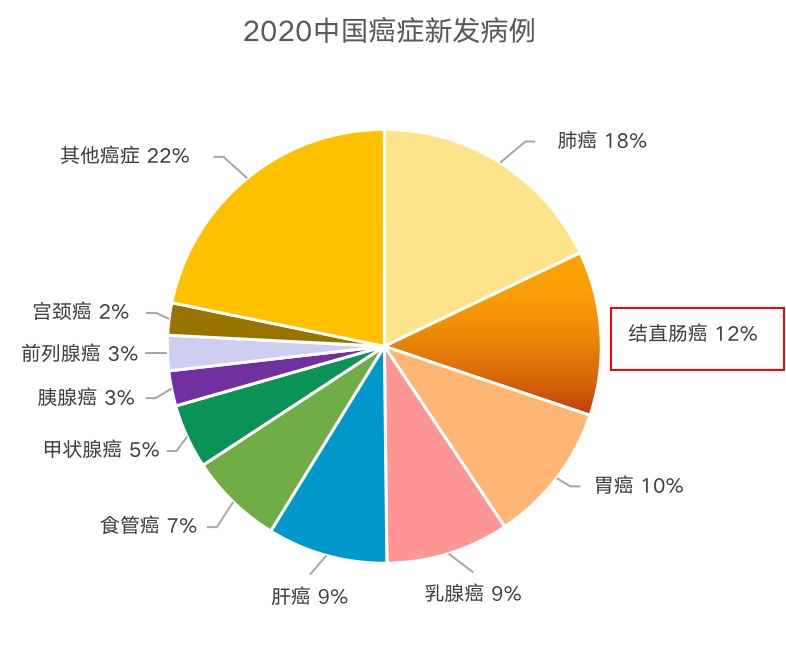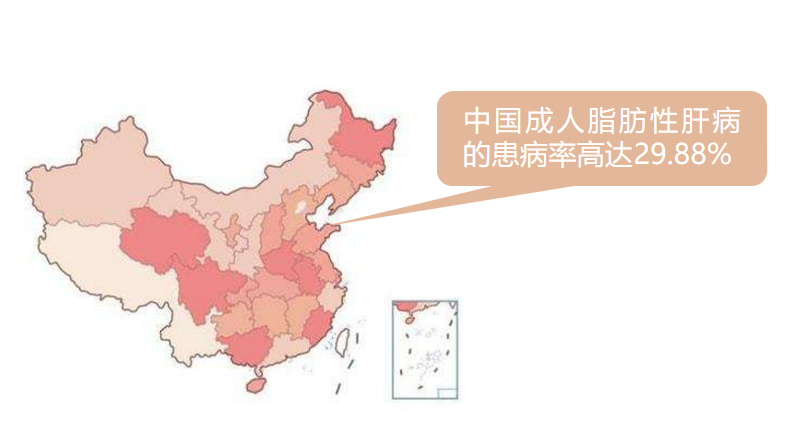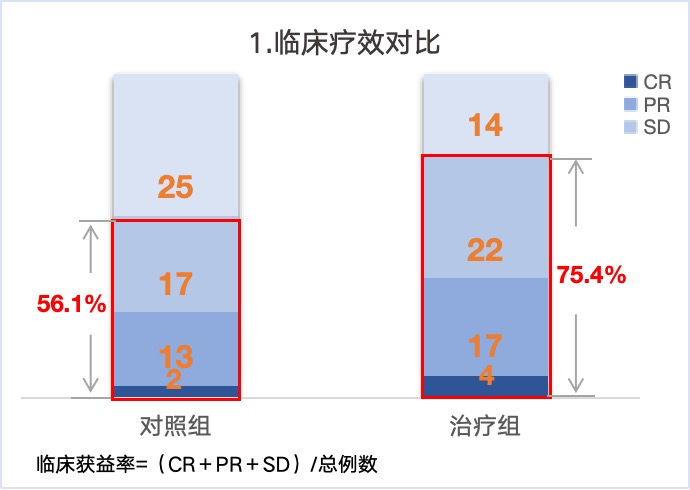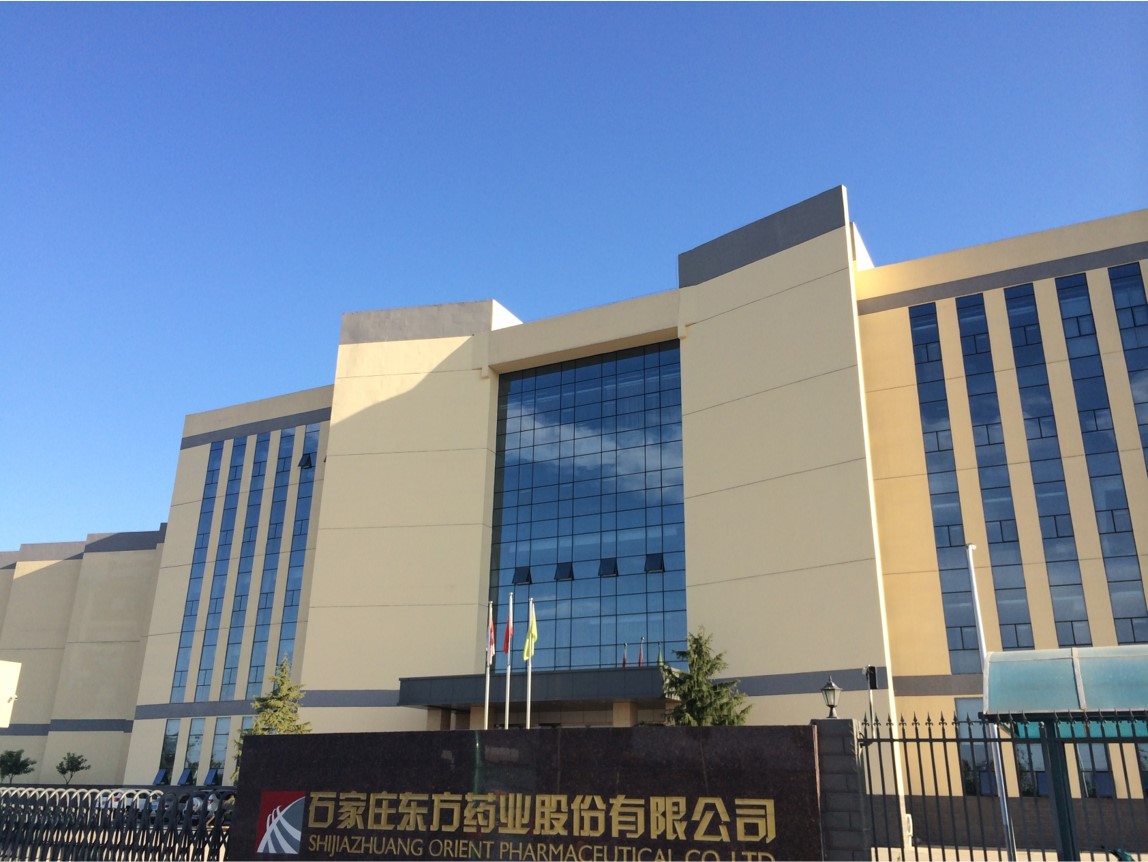dogwhelks在缅因州的天鹅岛海岸的框架上饲料。一项新的研究记录了这些和另外三种的潮流的衰落 - 至少部分地是气候变化。
来自缅因州天鹅岛的研究的二十几年数据文件缓慢而稳定地Dwwindling的贻贝,藤壶和蜗牛。
缅因州湾的水域几乎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比海洋更快地变暖。随着二氧化碳水平在大气中升高,它被海洋吸收,导致pH水平下降。海洋酸化使得贝类难以加厚它们的贝壳 - 他们对捕食者的主要防御。
在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Peter Petraitis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退休生物学教授,加州州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诺尔奇的生物学教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了博士队与Petraitis完成了博士后团契20世纪90年代,表明,不断变化的气候正在对缅因州的海洋生活造成损失。几十年来收集的数据集,包括五种贻贝,藤壶和蜗牛的数量,表明所有人都经历了下降 - 有些缓慢,一些速度更加迅速 - 部分由于气候变化。
“由于他们有多普遍,这些物种往往被忽视,”Petraitis说。“他们只是在岩石海岸的各处。人们不会想到任何事情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他们每年下降约3%,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变化,所以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段时间。但是一年来,人们会突然环顾四周,说'所有蜗牛,贻贝和藤壶在哪里?“”
Dudgeon表示,这些物种在缅因州湾湾的珊瑚礁中的核心“。“五种物种的并发下降,包括本土和非本土,比例大,可能导致该地区沿海海洋生态变化。”
1997年,Petraitis和Duckon在缅因州湾岛的海湾设立了一个长期的实验,研究了多个稳定状态的生态原则。Petraitis的研究和2013年的主题的重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多个稳定状态”,概念封装了生态系统可以在鉴于正确的环境扰动的完全不同的生物组合物之间快速切换。
对于天鹅岛上的贝类,当周期强大的冬季风暴导致海冰刮掉岸边的所有有机体时,发生了一种这种扰动,迫使社区从明年重建划痕。
1996年,Petraitis和Duckon通过刮掉岩石来模拟一场巨大的冰水冲洗事件,看看岸边的重新凝结会发生什么。从那时起,研究人员一直在天鹅岛上的60个研究情节进行年度之旅,计算不仅在刮在刮痕区域的生物的发生率,而且在其自然状态下留在左侧的地区,控制图。
目前的工作利用了这些控制情节计数,看着五种常见的贝类物种:玳瑁爵士(Testudinalia Testudinalis),普通的腹部(Littorina Littorea),Dogwhelk(Nucella Lapillus),蓝贻贝(Mytilus Edulis),和栏杆(半圆锥野生Balanoides)。
“我们没想到的是控制情节的变化很大,”Petraitis说,“但我们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口下降。”
从1997年到2018年的丰富数据,研究人员发现,非常年轻的贻贝在最锋利的自由落体中,每年跌幅近16%,而另外四种物种每年被削弱3%至5%。在那个时间段,跛行,悬崖和狗的总数下降50%,研究人员描述为“Sobering”。
为了获得为什么,研究人员展示了海洋温度和化学的数据。他们发现,贻贝的向下轨迹和共同的悬垂术争随着从附近的浮标收集的夏季海洋温度的增加而匹配。
与此同时,在石英座和节奏的群体中,与神经内饱和状态的增加相对应的,其测量与海洋pH轨道相对应。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较低水平的亚体饱和度与更酸性的海洋水域有关,这使得贝类越难以建立它们的壳。“这可能表明在近岸区域的其他条件,与文桥饱和状态不同,”Petraitis说。
颗粒号的变化与海洋温度,pH或横梁饱和状态的变化不相对应,这表明其他因素在其下降时扮演。
这些物种中的所有五种在缅因州的湾都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
作为过滤器,贻贝和藤壶从水柱中去除浮游植物,“消化它们,划分它们,施肥,施肥,岸上,”Petraitis说。在藻类和海藻上饲料的纤维素和周围饲料,所以更小的数字可能导致藻类盛开和“更环保”的近岸地区。
由于所有五种物种作为各种动物的猎物,萎缩的人群将会混淆食物链,也影响人类。
“没有动物消费转移有机质,”食物网,“迪尔顿说,”沿海海洋的生产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微生物生物分解的途径分流,而不是支持人类鱼类和沿海经济的种群依赖。“
Petraitis还注意到普通的腹层,现在是海岸的象征,被引入19世纪中叶的缅因州湾湾。“现在这是海岸上最常见的格拉西尔 - 他们像山羊一样喂,”他说。“在1860年之前,没有芙蓉的岸边可能看起来比现在更绿。随着他们衰落,我们可能会看到岸边在1850年代恢复到其州。“
在过去几年的会议上展示了这些调查结果的同时,Petraitis说他从其他科学家那里听到了关于北大西洋的贻贝类似消失的轶事,这表明该现象并不孤立于缅因州湾。
参考:“在西北大西洋的过去二十年中,彼得·彼得斯·彼得·彼得·迪尔德·迪尔顿2020年10月20日,通信生物学迪尔斯·迪尔顿迪尔迪尔·迪尔莫利:
10.1038 / s42003-020-01326-0.
Peter Petraitis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在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生物学学院。
Steve Dugderon是加州州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诺尔德里奇。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GRANTS OCE-9529564,DEB-0314980,DEB-1020480和DEB-1555641)的支持。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