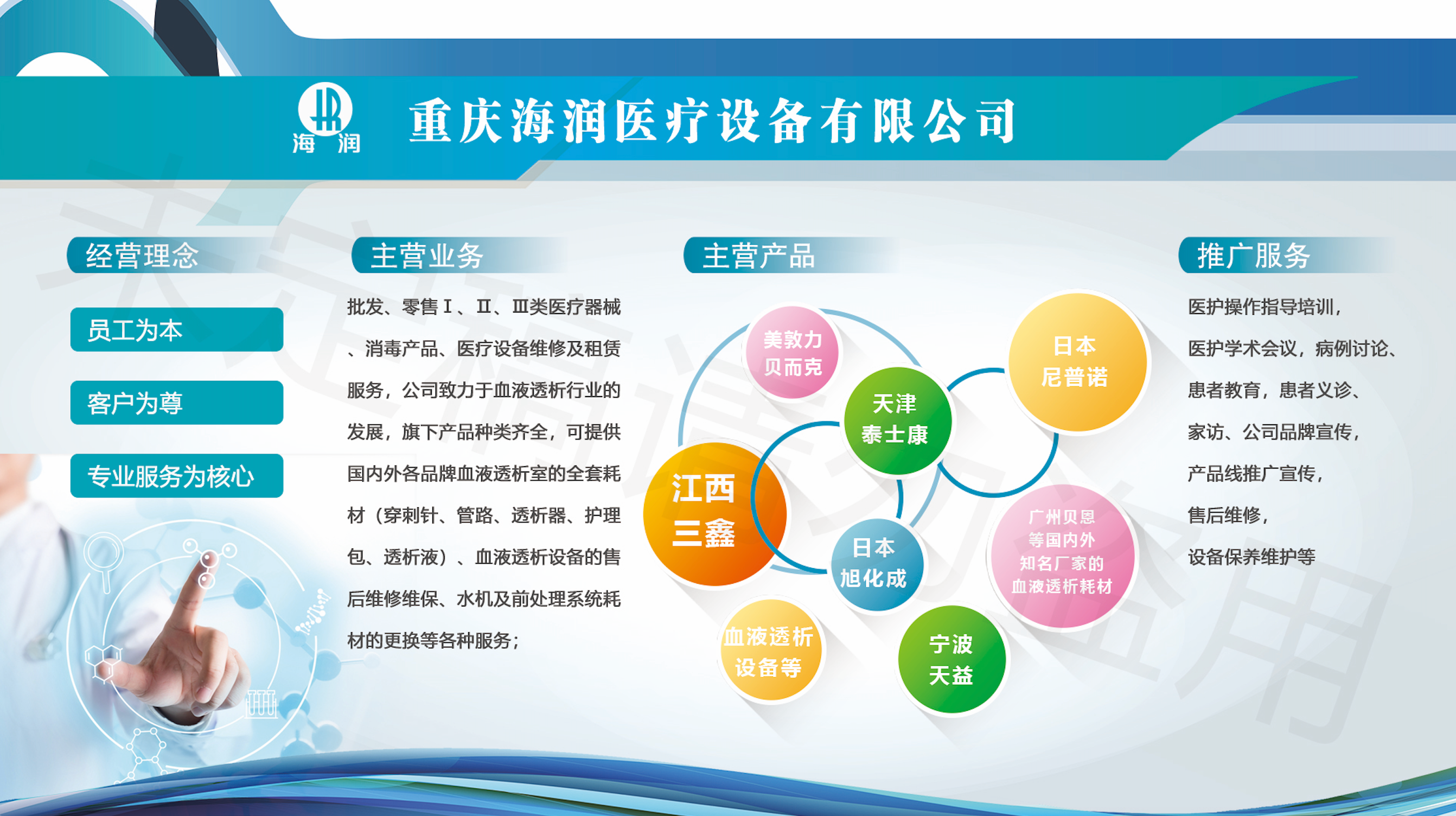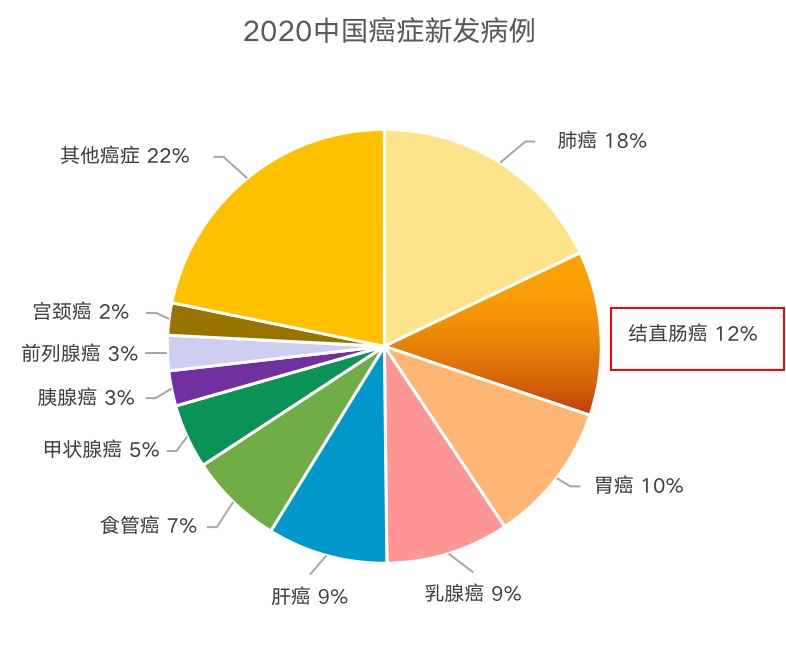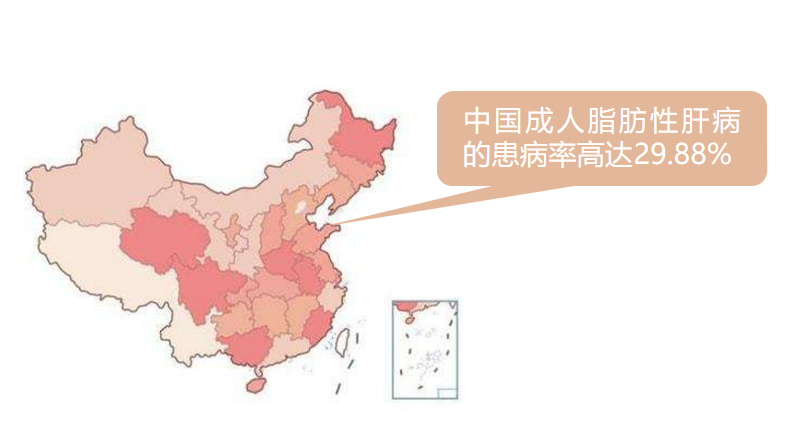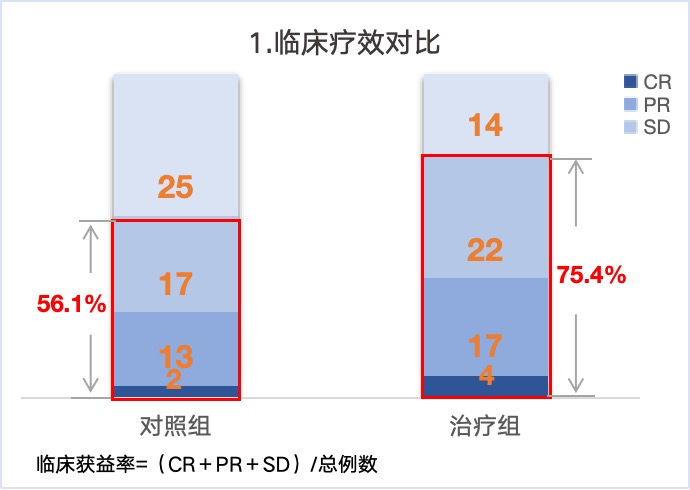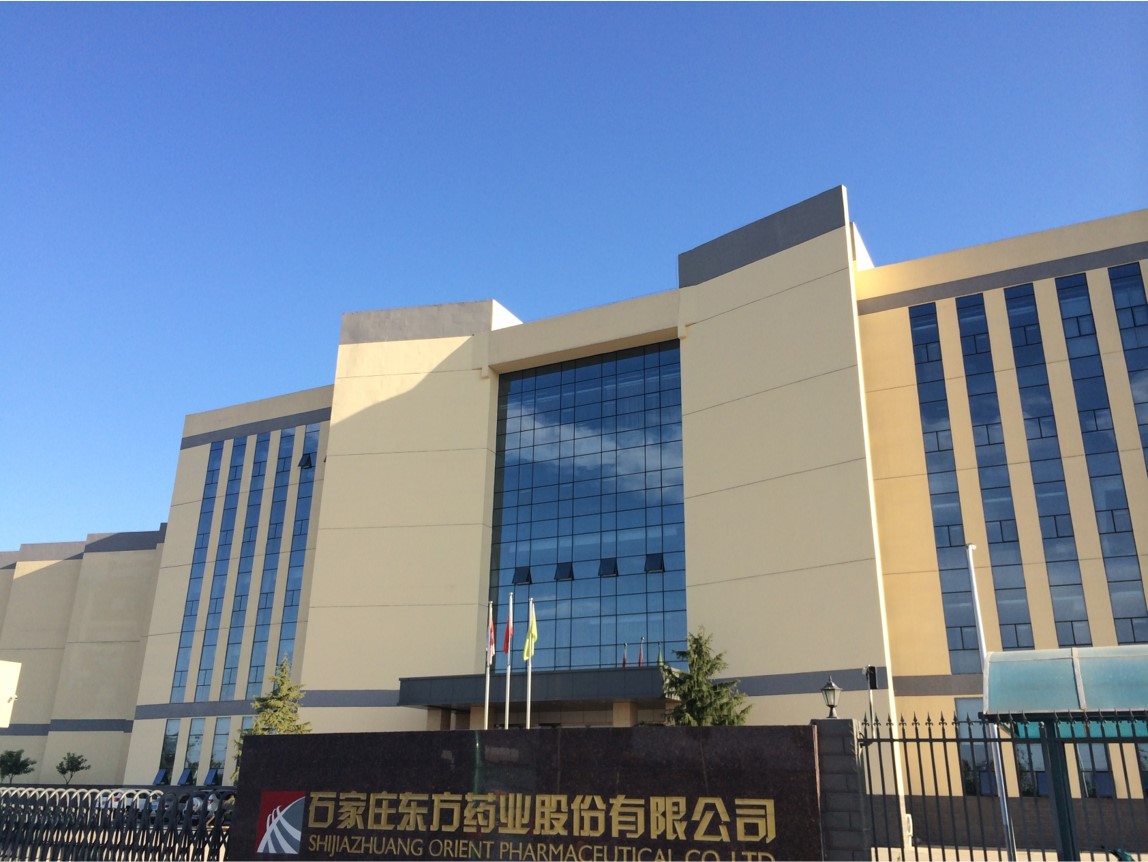虚拟STARR论坛,“岩石上的民主国家?”包括专家讨论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主的命运。从左上方顺时针方向:Neeti Nair,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副教授;苏珊亨西伊议员的立法执行编辑;主持人Richard Samuels,福特国际政治科学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伊顿·迪伯(伊顿)教授哈佛大学政府科学教授;哈佛大学政府教授Steven Levitsky。
专家分析了全球趋势:在维护合法性贴面时,民主政府在内部崩溃。
当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时,它似乎民主在政治系统中胜过。但最近,许多民主国家都遇到了一套常见的烦恼,有专制领导人掌握了足够的力量来创造非自由制度。
了解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MIT于2020年10月23日的焦点,STARR论坛(见下面的视频),由国际研究中心(CIS)托管的在线活动,其中一系列专家评估了全球民主的状况。
“民主国家不会死于他们曾经死的方式,”哈佛大学政府教授史蒂文·莱维茨基说,在虚拟事件期间。“民主国家用来死在枪的男人手中。在冷战期间,每四个民主崩溃中的三个是经典军事政变的形式。… 今天民主国家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死亡。他们死在手里不是将军,但选出的领导人,总统,谁用民主的制度颠覆它总理“。
事实上,虽然在美国民主困难的困难中往往会营造一个“宪法危机”,这可以是一个“非晶学期”,未能解决长期政治动态,注意到苏珊轩尼诗,法律博客的执行编辑,法律研究所的总法律顾问,以及国家安全法院的布鲁金斯。
“在美国,我们经常认为它是一个离散的促进事件,其中宪法秩序受到危险,然后宪法秩序恢复,”亨斯约州说。“这一刻更有用的类比是宪法腐烂。我们不太可能面对一个对系统抹去的单一事件。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缓慢的侵蚀。“
STARR论坛是全球事务和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期赛事。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在CIT和CI总监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受到了讨论。
星期五的小组成员是莱维茨基; Hennessey,谁也是共同作者(与本杰明Wittes)的书籍“未揭露主席”(2020年);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副教授Neeti Nair,是“改变家园:印度政治和印度的分区“(2011);而丹尼尔·ZIBLATT,也是哈佛大学政府教授,并于莱维茨基于“民主国家决心如何”(2018)。
在他的开场白,塞缪尔斯指出,“当选的领导人通常都颠覆民主机构,并允许民主滑向专制。… 这位顾客了解原因。这位顾客了解如何。“
Levitsky建议“幻灯片”通常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当选独裁者”将启动“捕捉裁判”,即,在执法,法院,情报部门,税务机关,多变化的人才。然后,忠诚主义者挥舞着政府权力,独立行军反对派的权力。最后,通过关于Gerrymandering,竞选金融和媒体访问的新规则,独立“改变竞争领域”。
在这些政治中,出现的是“有竞争力的威权主义”,莱维茨基说,“游戏领域相当偏向反对”。看着全球,他补充说,“匈牙利是一个明确的案例。委内瑞拉,也许波兰,也许是印度,希望不是美国。“在他看来,这种结果通常会发生在民粹主义者在没有感受到民主的情况下实现重大选举队伍的时候 - 如秘鲁,委内瑞拉,土耳其和厄瓜多尔的当前和过去的制度 - 或者当政治派别说服自己时,他们必须限制民主才能保持权力。
在后一种情况下,在美国南之后的重建之后,Levitsky指出,各国增加了广泛的投票限制,旨在非洲裔美国人,包括民意调查税,识字税和财产要求;该地区的黑道岔从1912年的1880年下降了61%至2%。
尽管如此,每种情况都不同,Ziblatt指出,他的言论在德国魏玛沦陷。虽然他观察了“极端情况”,但他观察到的,德国“遗留措施,在我们对民主讨论中的所有讨论”及其保障。
“魏玛经验暴露了民主的深厚脆弱性,”Ziblatt说:“选民可以选择一个专制的权力。民主可以在投票箱中死亡。“但是,他补充说,精英也可以被赋予:纳粹党从未得到超过约30%的选民的支持,但德国保守派通过与希特勒形成联盟进行了命运错误,以试图使他边缘化。
“当专制人士来到权力时,他们不在自己进入办公室,但随着政治成立内部的政治盟友的支持援助,”ZIBLATT说。“这是魏玛崩溃的中央课程。这是一种精英错误分布。“他同样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他指出,墨索里尼据称,墨索里尼据称通过他的“罗马的3月”抓住了权力,但实际上与Victor Emmanuel III的谈判协议给了意大利在议会的法西斯席位。
“我不想尽量减少法西斯和尊敬的社会运动的力量,”Ziblatt说。“他们是真的,今天是真实的。我的观点只是,当极端分子首次到达现场并似乎威胁民主时,应该认真对待,边缘化的主流政治…家必须尽一切可能形成联盟,甚至有时与他们可能不同意或不同意的缔约方有时非常不舒服的联盟,但谁接受了比赛的基本民主规则,以保持极端分子。“
为了确定,有时候熟悉的PS获得权力和研究所的实质性变化 - 正如我们对印度和纳伦德拉·莫迪的言论在印度民族主义愿景周围定向最近政策的言论中的Nair,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Nair说,总理“不会陷入局外人的原型,他被允许通过建立政治家的守门人领导政党,这些政治家应该知道更好。”Nair补充说,印度现在有“法律规则是极端无人性的封面的空间”,但她在一个更乐观的票据中得出结论,朝着国家的政治可能再次转移时朝着可能的2023年选举。
“我认为印度是因为它的许多区域政党可以在过去,它的普遍存在的佩戴和强大的民间社会,最近在抗议2019年的公民法案期间的证据,[和]其独立的媒体“仍…然有些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承受这种最新的危机对民主,”Nair说。
看着美国,Hennessey强调了该国的创始人赋予主席的显着广泛的力量,其中许多人通过规范维持自己,例如基于基于基于主席团的主要执法职位的传统,以及许多总统任命的国会批准。
已经有了,最近亨西的注意到了这些做法的“真正令人震惊的侵蚀”。因此,她补充说,“仍然存在,流程仍然存在,我们仍然存在,我们仍然观察到宪法体系的技术性,但他们挖空,而且他们不仅仅是他们的合法性,而且他们不再履行他们的宪法目的。“
下周的大选,亨斯利观察到,因此,就行政部门职能,政府分支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系统近几十年的稳健性而言。
“选举是一个非常钝的仪器,”亨西州说。“这是我们批准或拒绝这一总统愿景的时刻。”
了解民主本身轨迹选举的意义是积极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今天的许多人在全球治理的同样变化不是街道上的坦克,而是从利用结果投票箱。
“它发生在一个非常可靠的民主外观之后,”莱维茨基说。“许多公民都没有完全了解发生的事情,直到它为时已晚。”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