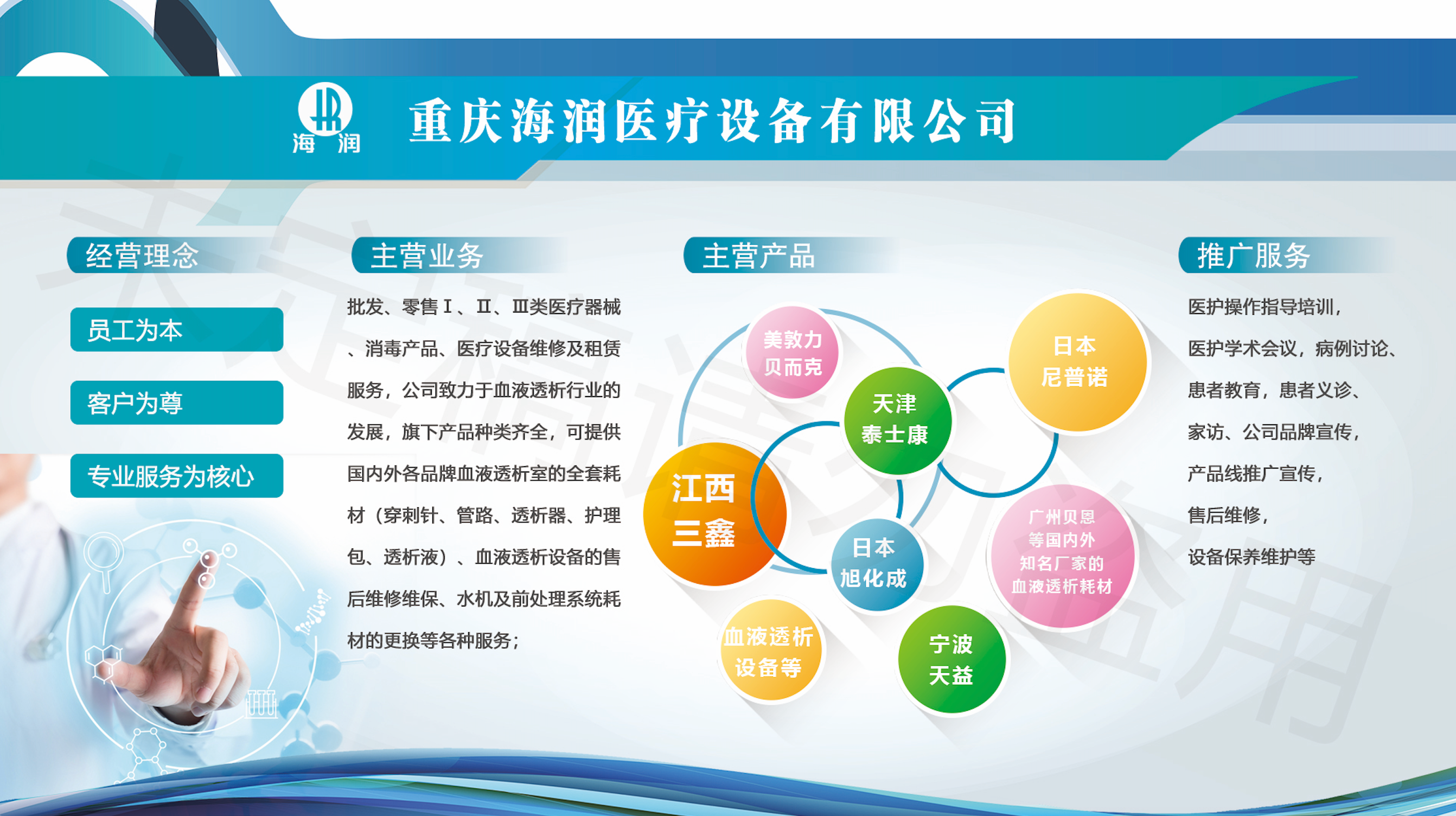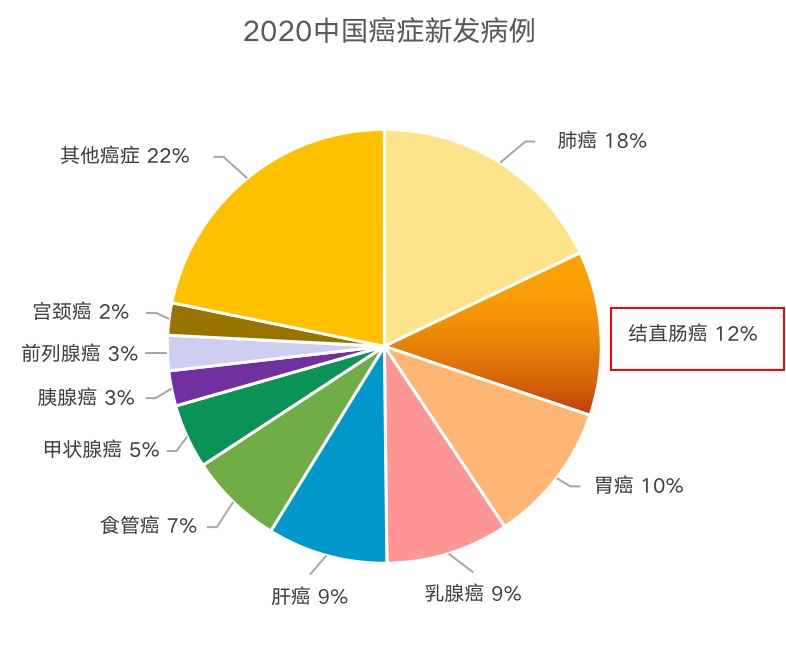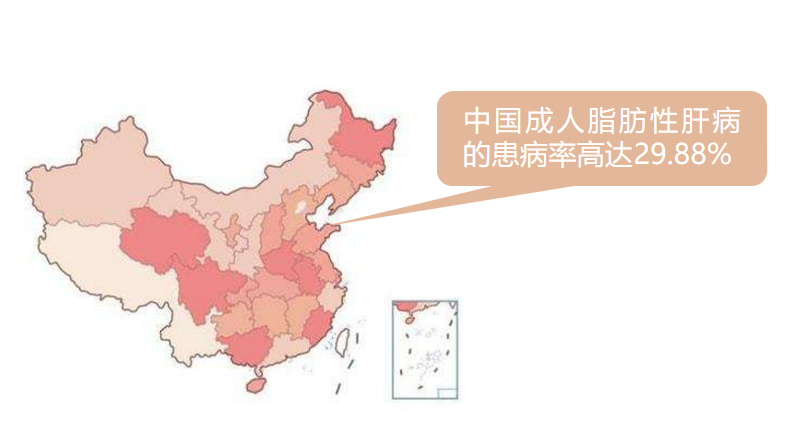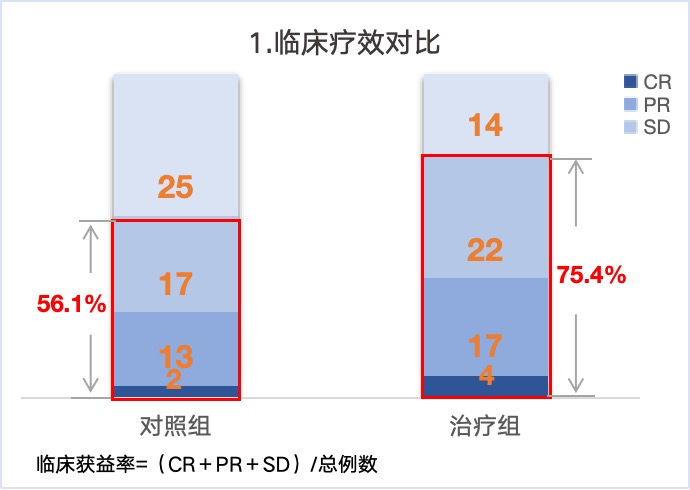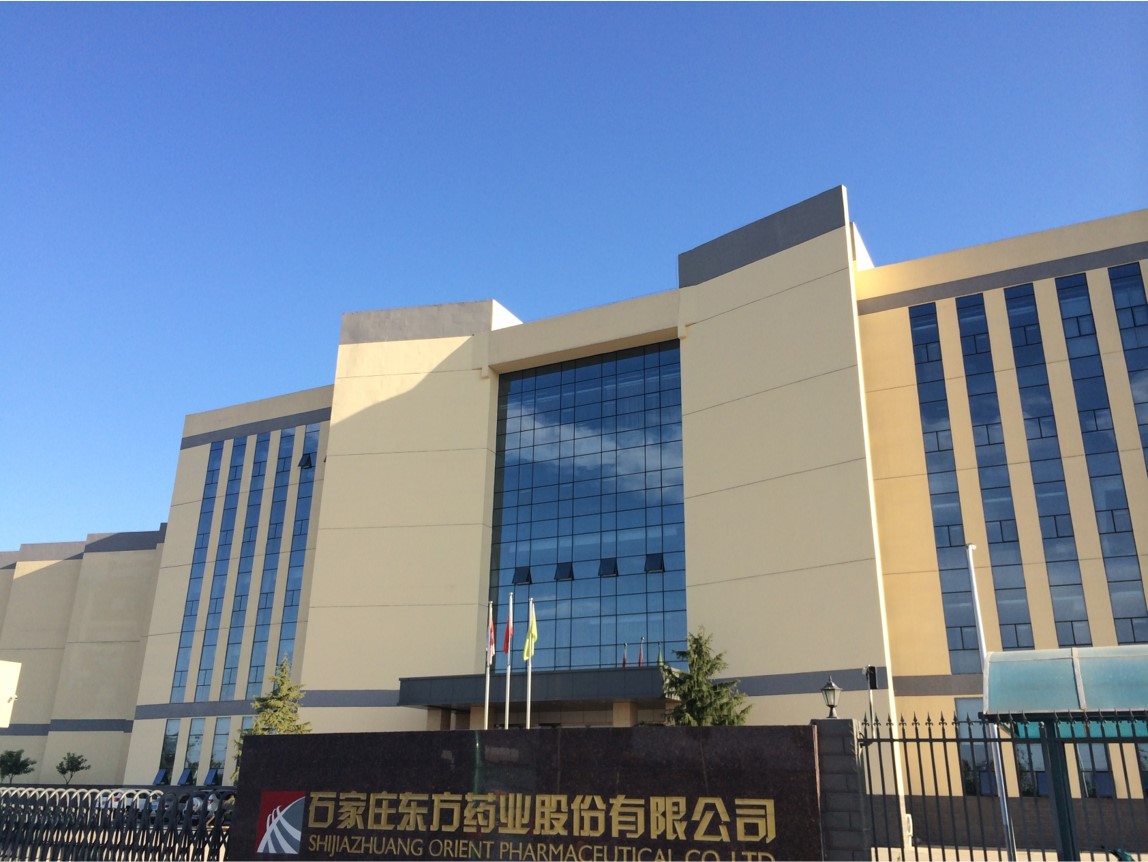医疗消费者中心主任阿瑟·莱文(Arthur Levin)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杀手,如果我们称呼它这么高的死亡率,还需要像SARS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将付出巨大的国家努力。” 。
1999年IOM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Robert M. Wachter,医学博士在一次纪念该报告的会议上说,有证据表明医生对患者安全的态度或安全本身已经得到改善的证据“并不惊人”。
几个州现在有法律规定,医院报告有可能伤害患者的医疗错误和“近失误”。但是,许多医疗错误不仅是医生或护士的错误,而且是在人满为患的医院中过时的记录保存和处方系统的错误。
“有很多报道。他们坐在某个地方的架子上,还没有转化为行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系副主任瓦赫特说。
安全药物实践研究所所长艾伦·韦达(Allan Vaida)表示,自1999年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指出,联邦监管机构和药品生产商现在更快地响应有关药品名称或包装可能引起混乱的警报。
“人们在听。”瓦达说。
但是,决策者们仍在努力寻找方法,要求不称职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承担责任,同时又不容许惩罚威胁扼杀医疗错误报告。
医生抵抗?
医生也可能拒绝推荐促进团队式培训的建议,医生,护士和其他人员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单位,以减少医疗错误。飞行员通常会使用类似的系统,并且该系统可提供制衡功能,有助于减少驾驶舱错误。
瓦赫特指出,一项调查显示外科医生的人数是飞行员的五倍,他们决不应该质疑他们的决定。他说,尽管团队培训是在隔离的卫生系统和医院中进行的,但培训并不广泛。
波士顿医疗保健改善研究所所长卡罗尔·哈拉登(Carol Haraden)博士说,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医生,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的反应迟钝。“对结果必须有某种责任感和道德上的愤怒,我认为我们还没有那种感觉。”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