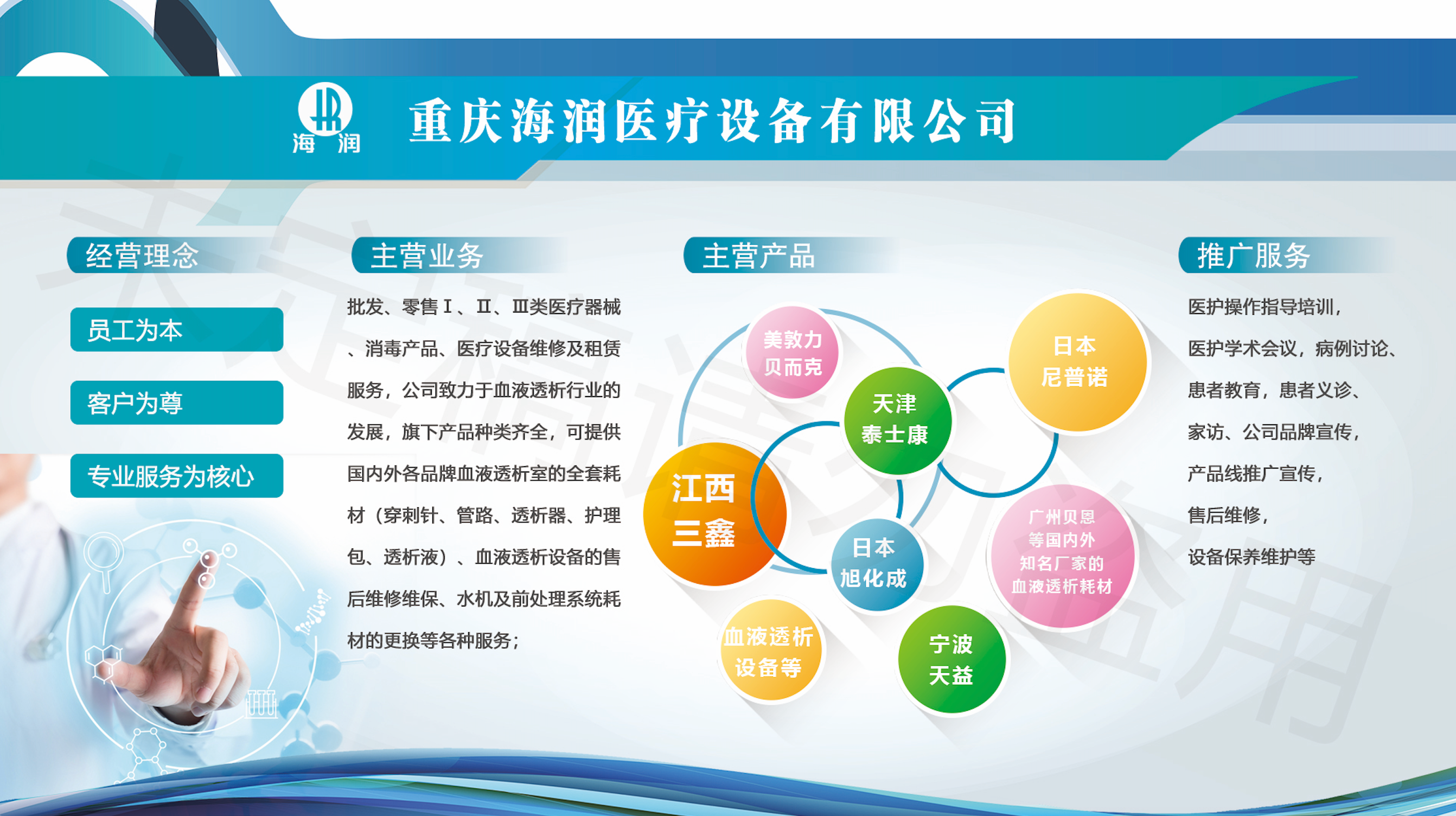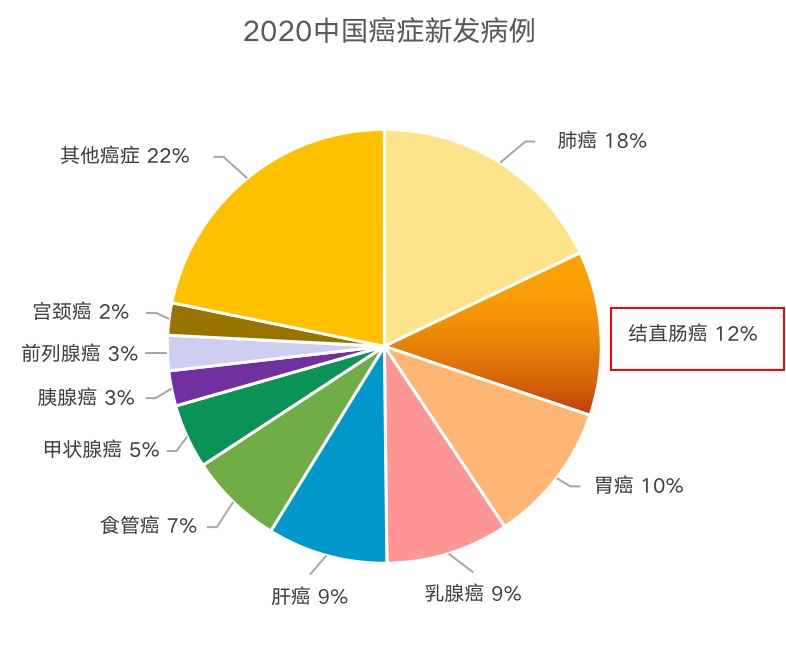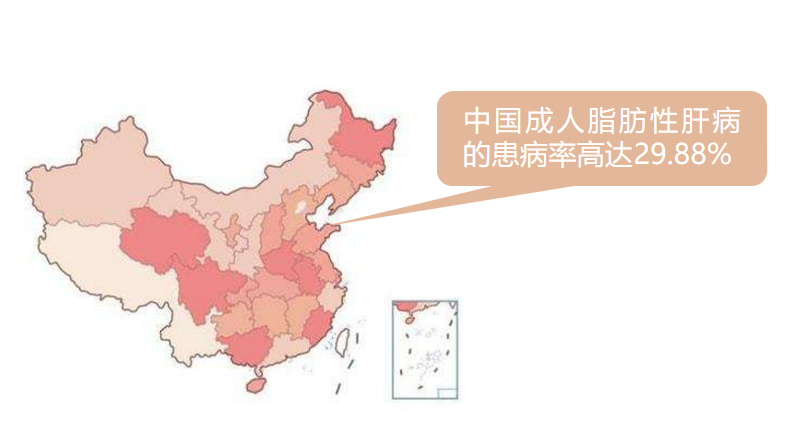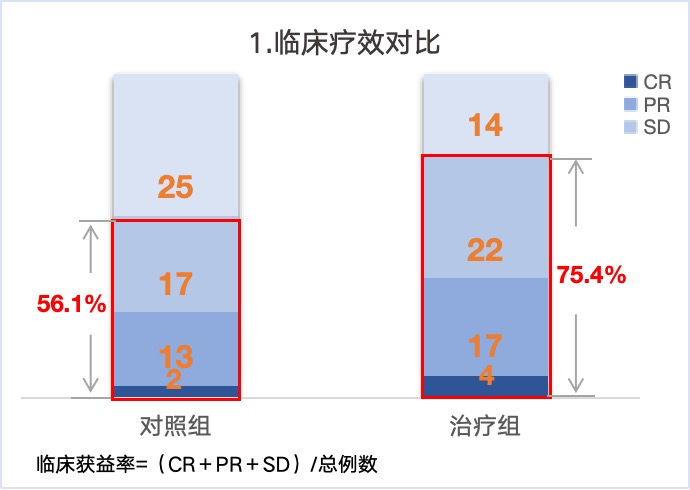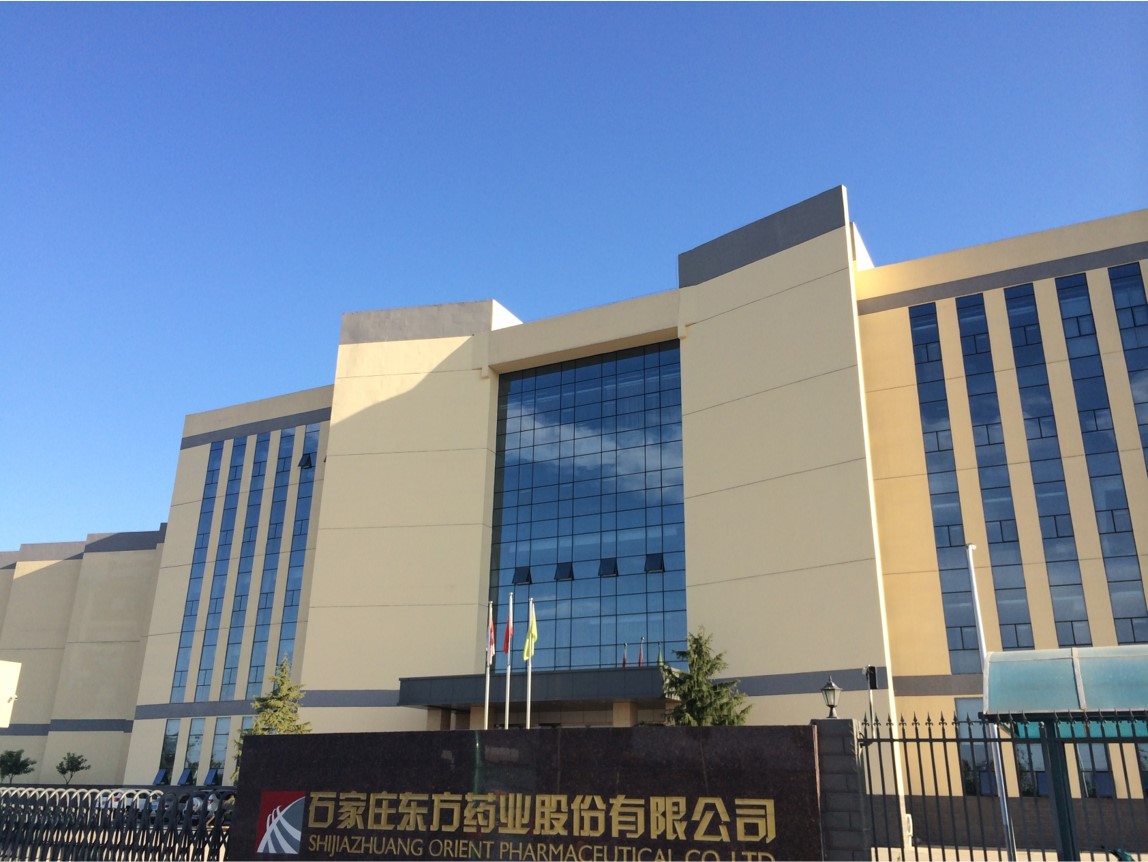Wanga Zembe-Mkabile从别人厨房里的不适中学到了很多东西。2009年,南非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正在为其博士学位收集有关政府儿童抚养补助金结果的数据。这项研究要求“盘点库存”来对研究参与者厨房中的食物进行盘点。但是看到人们打开常常空着的厨房后,一个又一个的家中的尴尬,Zembe-Mkabile感到有些不对劲。她说:“这只是觉得进入人们的橱柜是正确的。”
当时,她没有为自己的不安采取行动。仅仅几年后,作为一名知名科学家,泽姆贝·麦卡比勒才开始理解自己的忧虑之情。基于社区的研究通常会使年轻的科学家处于对研究参与者的控制权上,这一角色可能令人生畏和陌生。但是对于Zembe-Mkabile来说,这种感受更加深刻了。她了解种族隔离,以及种族隔离的建筑师如何利用科学来支撑种族主义哲学。她在厨房中遇到的那种权力失衡的痕迹依然存在。
Zembe-Mkabile在贫穷中成长,但作为一名在英国牛津大学接受培训的科学家,她是白人欧洲人为之塑造的体系的产物。这两个角色(“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她作为研究者的身份至关重要,并影响了她对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进行研究的思考。现在,她在开普敦的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工作,指导有关社会政策与贫困,不平等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她计划在实验的设计阶段让社区参与进来,并最终将其也纳入分析中。如果她已经觉得工具或问题不适合其设置,则可以将其从研究中删除。她说:“有些问题如果要践踏人们的尊严,就不值得探讨。”
詹贝·麦卡比勒(Zembe-Mkabile)考虑到自己国家对学术界非殖民化的呼声日高时,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很多思考。非殖民化运动是消除或至少减轻了欧洲白人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中不成比例的遗产的运动。据倡导者说,这不仅是增加黑人科学家的人数,尽管这种种族“转变”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消除欧洲价值观的霸权,为殖民者抛弃的当地哲学和传统让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文献支持更改课程的需要,并且一些南非大学已开始采取行动并建立审查委员会。但是,推动变革有时是紧张的。学生示威活动将关于非殖民化的论据包装成对大学费用的抗议活动,并导致班级混乱,火灾和数百万美元的安全和维修费用。
科学部门努力定义非殖民化对他们的课程和研究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正在加紧努力,以克服黑人科学家人数众多的明显不足,但是接下来还不清楚。横跨种族隔离前和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的Zembe-Mkabile一代将很快成为国家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将为新的南非重新制定科学挑战。
榜样
与许多国家一样,南非目前正在处理高失业率和明显的不平等现象。种族隔离统治的遗留下了这些焦点。尽管自24年前南非民主制度诞生以来,政治权力就一直由黑人控制,但白人仍然拥有经济权力:2015年,白人家庭的收入约为黑人家庭的4.5倍,白人拥有60多个黑人尽管仅占工作人口的10%,但仍占最高管理职位的百分比。在大学中,尽管占人口的80%,但黑人在学者中所占的比例却不足35%。同时,学生面临成就的多重障碍,其中包括教育系统,使许多人没有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2015年的政府报告发现,南非黑人的辍学率最高。 32%的人在第一年毕业。在课程方面,非洲文学,哲学,医学和文化常常被贬低为选修课程或完全被忽略。
在此背景下,Zembe-Mkabile一代的研究人员开拓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种族隔离时期的儿童,他们在1990年从监狱释放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彩虹余辉中长大成人。有些人来自对科学不信任的社区。在Zembe-Mkabile的家庭语言Xhosa中,甚至没有一个词可供研究。她说,最好的近似是ukuphanda,它具有负面含义。她说:“这意味着寻找坏事,例如进行警方调查。”
Zembe-Mkabile一代的科学家是1994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榜样,他们在当地被称为“自由出生”。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1,预计这一代人将在2025年之前将黑人研究人员的国家比例提高到50%以上。对于像Zembe-Mkabile这样的人来说,沉重的负担挤在了训练他们的学术体系的要求与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年轻人的期望之间。Zembe-Mkabile说,当她还是学生时,抗议大学中的不平等问题并没有摆在桌面上。“渊ou进入了这些空间,您很高兴能在那里,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我们快睡着了。至少现在,学生们保持警惕。
非思想化
Zembe-Mkabile的体验并非独一无二。Grahamstown的Rhodes大学的学术开发人员Amanda Hlengwa对她1990年代后期在德班的大学学历有类似的回忆。他的目标是同化。她说,这是不断变化的趋势:大学正在开始认识到学生的多元背景以及大学文化所带来的挑战。但是,解决这一差距的策略实施起来很慢,执行起来也不均衡。
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哲学家Thaddeus Metz表示同意。他是一位白人美国人,于2004年定居南非。他是第一位在附近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授非洲哲学的人。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是该市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在此之前他就职于该大学。他说:“这种长期以来的知识传统充其量是被最好的方法所忽视,最坏的情况是被贬低了。”他补充说,大多数学生,不论种族如何,都对非洲的知识传统感到好奇,但缺乏机构领导。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人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们感到孤立无助。
在自然科学中,它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非殖民化的含义尚未明确定义,并且其相关性受到质疑。非殖民化科学是否意味着要抛弃艾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和格雷戈尔·孟德尔,并从本地知识重新开始?开普敦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一个校园讨论的在线视频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该视频的标题是“必须降下科学?”。梅斯说他遇到了争论。“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如果某种东西来自非洲,那么它就会以某种方式取消比赛资格。”?/ p>
但是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持有如此激进的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的非殖民化需要更复杂和微妙的东西。前心内科讲师,现在在大学管理领域工作的西亚达·马考拉(Siyanda Makaula)说:“思想上将发生令人沮丧的殖民化。”这种思维上的转变可能意味着,例如,药理专业的学生会听到祖母用来治疗胃痛的植物是如何开发药物的。这将显示传统文化在现代科学中的相关性,并将课程锚定在当地经验中。在其他主题中,这可能是关于突出非欧洲人的贡献,或者是面对一门糟糕的学科历史:例如,探索医学研究如何在助长种族主义思想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挑战和推翻这些思想。全面而言,这意味着确保研究能够解决本地问题和挑战。
马卡乌拉认为,科学家经常将自己的学科“公认的普遍性”隐藏起来,即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细胞,无论它是属于非洲还是属于欧洲,或者物理定律都适用于所有细胞,从而避免了对物质的质疑。他们做事的方式。他说:“这是他们使用的借口。”但他补充说,科学的意义在于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说,为此,背景必须成为科学教学的一部分。“关于您如何教授它,如何应用它,如何使它具有相关性,以便人们可以接受它并更好地吸收它。”?/ p>
Makaula说,这种重新定位在南非的大学中花费了太长时间。就黑人研究人才而言,这种惯性正在使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年前,Makaula获得了心脏病学博士学位。但是,在他的白人同事可以留在实验室的同时,一再要求种族歧视和象征主义的刷子,以及其他黑人学生会见潜在的资助者,这使他沮丧,以至于他离开了学术界。如今,他为位于比勒陀利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是一个公共部门机构,负责大学的质量控制和法规遵从。
从表面上看,南非的大学正在努力使其学术服务非殖民化。大多数人都成立了委员会来审查他们的课程,尽管很少有人对此有所作为。所有人都受到政府和资助机构的压力,要求他们培训和聘用更多黑人学者。研究资助者正在效仿。几年前,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将其最大的资助计划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早期职业科学家,并增加了性别和种族的权重。此后,用于白人调查员的赠款比例从2012年的72%下降到2016年的37%。该委员会主席格伦达·格雷(Glenda Gray)表示,该委员会还正在就非殖民化问题发表立场声明,以加强其招募黑人科学家的努力(见“三种文化”)。它将研究医学研究如何利用社会科学对社区需求变得更加敏感。“只有当您了解生物学发生的环境时,渊源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p>
“黑人妇女的去处”?/ b>
一些南非人将非殖民化作为重新发现其遗产的一种方式。开普敦附近的斯泰伦博斯大学的生物技术专家Nokwanda Makunga在知识界长大,引起了反种族隔离的自由战士,如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Makunga从小就完全知道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她的早期记忆之一是帮助父亲-一个植物学家-算出玉米(玉米)的谷粒用于实验。在种族隔离的垂死岁月中,她参加了格雷厄姆斯敦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那里的种族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因此,当她于1990年到达政治上脆弱的省Pietermaritzburg的大学(现在称为夸祖鲁-纳塔尔省)时感到震惊。“来自非种族,非政治的泡沫。然后我被带到了真正的南非。她的高学历和剪短的私立学校元音使她以“白人”的身份被选为黑人学生。但是对于白人学生来说,她也太黑了。“泪从两端得到。”?/ p>
三种文化
黑人研究人员正迅速进入南非学术领域。但是,国家高等教育和培训部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足”。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却被归类为“外国人”。
它是一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一份报告4发现,尽管黑人博士毕业生在2012年的南非历史上首次超过白人,但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尼日利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家。
有几个原因。在南非学习比在欧洲或美国便宜,并且该国提供比非洲其他地方更好的研究设施。但是对于某些当地人来说,外国黑人研究人员的日益增多是一个问题。职位稀缺,有些人认为大学比本地人更愿意雇用非南非黑人。
因此,外国黑人科学家(例如驻德班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肯尼亚病毒学家Thumbi Ndung)经历了一种特殊的疏远。“渊国可以”完全认同当地的黑人人口。他们将您视为局外人。他说,另一方面,你不在白人白人男孩的“俱乐部”里。
恩东(Ndung)在2005年移居德班(Durban)研究艾滋病毒时曾预料到会有摩擦。但是直到他住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当地黑人学者的挫败感。他说,该系统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
Ndung自己的大多数研究生是南非黑人。他说,它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在正确的支持下,它们会蓬勃发展。“需要在这里做出明确的努力,以使它们进入系统。因此,南非的大学将来不会再遇到这个问题。” / Linda Nordling
2004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后,Makunga向往更安静,更注重研究的机构。她得到了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的录取通知,斯泰伦博斯大学是一所全白人学校,坐落在风景如画的Cape Winelands。它提供了稳定性,并为Makunga建立国际声誉提供了平台。但从历史上看,它也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堡垒,曾产生过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时代的首相,例如亨德里克·沃沃德(Hendrik Verwoerd)和D. F. Malan。Makunga的一些朋友被吓坏了。内恩告诉我,斯泰伦博斯是黑人女性的无处可去。他没有说为什么,只是说那是非常保守的。Makunga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如果没有黑人妇女愿意去那里,黑人妇女将成为一个地方吗?” / p>
Makunga的研究使她更加扎根。她说,长大后,她的家人没有使用传统药物。但是现在她用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了南非的药用植物,以探索其药理特性。她认为这项工作是“相当殖民地的”。在研究了各种植物之后,她于2016年回到了长大的东开普省,学习了祖先所采用的传统医学。她认真对待这些做法的监护人责任。“泪”持有别人的知识。她说,我需要尊重它。
自从被警告以来,斯泰伦博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肯加说,她目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州大学获得为期9个月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她在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受到欢迎,并被认为是黑人女性-在教职员工中仍然很少见。不过,她仍然渴望那不是标题问题的日子;当她可以先是科学家,然后是黑人妇女时。她渴望地说:“泪水希望我们超越种族隔离种族的宿醉。”
黑人妇女是南非学术熔炉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他们占该国研究人员的14%,而黑人则为18%。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机遇。在她2015年的文章“领导力:非洲妇女的隐形性和权力的男性化Mamokgethi Phakeng写道2,黑人妇女以及白人社会因其性别和种族而被边缘化,他们面临着父权制非洲文化的反对。这种“权力的凝聚力”?她写道,需要与殖民主义和性别歧视同时受到挑战。
Phakeng是开普敦大学数学教育学者和研究副校长。她对黑人研究者经验的直率吸引了一批Instagram和Twitter追随者。但她感到,有时崇尚误导。激励年轻人大声说出来并成为自己,这真是太好了,“我不想让那成为我最有力的角色”吗?她说。
对她而言,她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一名研究人员。Phakeng的工作重点是数学和语言。例如,她证明了3“在语言之间交替”的代码切换有助于多语言人员理解数学概念。在南非,这是很重要的,那里的学生因为使用母语而受到责骂。如今,许多教室都鼓励代码转换。
然而,批评者认为,非洲最强大的科学机构之一的研究负责人的背景并不适合她。去年10月,一封电子邮件开始流传,质疑她的资格。她接管了攻击者,副总理马克斯·普赖斯(Max Price)谴责了电子邮件及其内容。
南非大学界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赫伦瓦担心学生抗议活动产生的势头可能会消失,而持续的变革不会扎根。她说:“在不断升温的同时,您还有机会进行课程改革。”她说,但是随着大学学会在动荡中工作,他们又回到了旧的方式。她还担心黑人学者对黑人学者的要求正在陷入困境-从被邀请参加多元化委员会到就黑人学生和教职员工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建议。“在这里我可以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深入思考吗?”赫伦瓦问。
这是一个负担,也是一个挑战。法肯认为,只有话语才能帮助它。自2016年中加入开普敦大学以来,她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黑人黑人学者交谈。她说,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管理层第一次要求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问人们,你告诉自己什么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我们做事的可能性。
自然554,159-162(2018)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