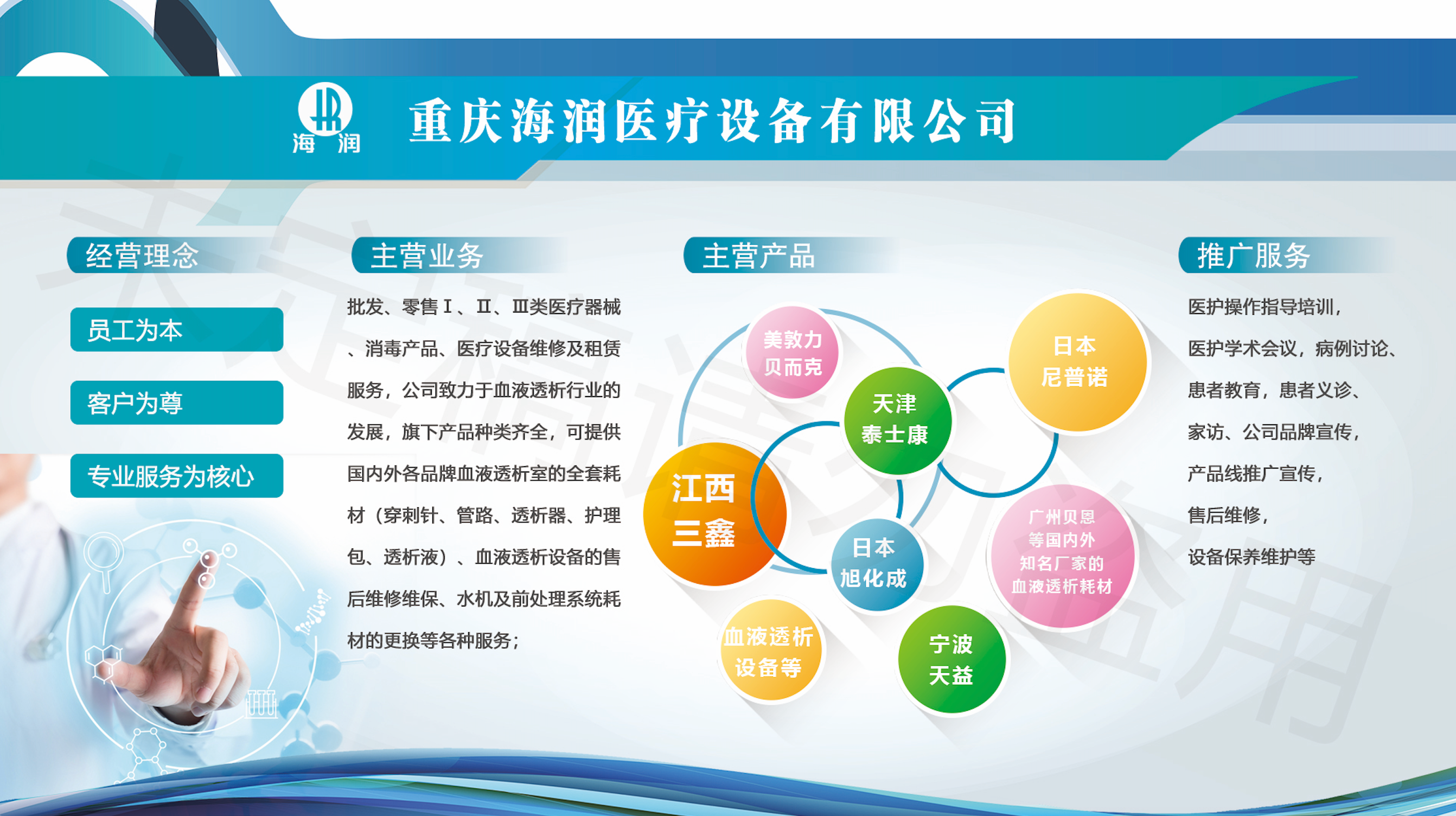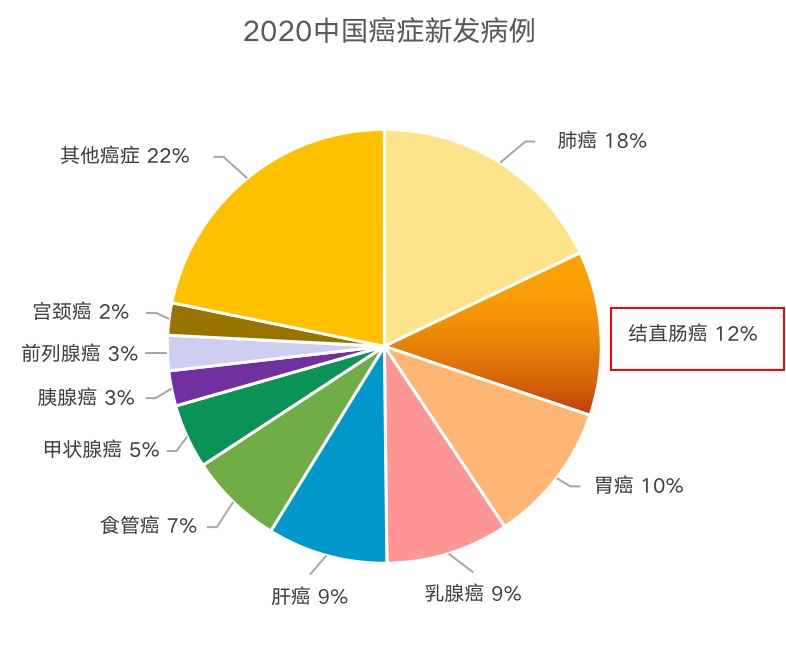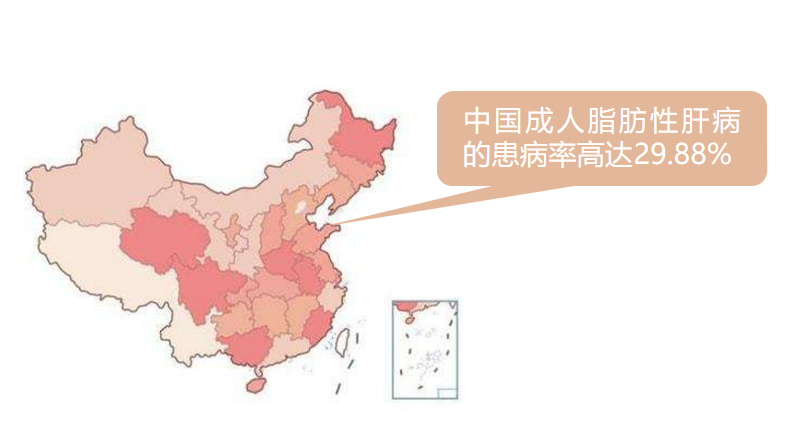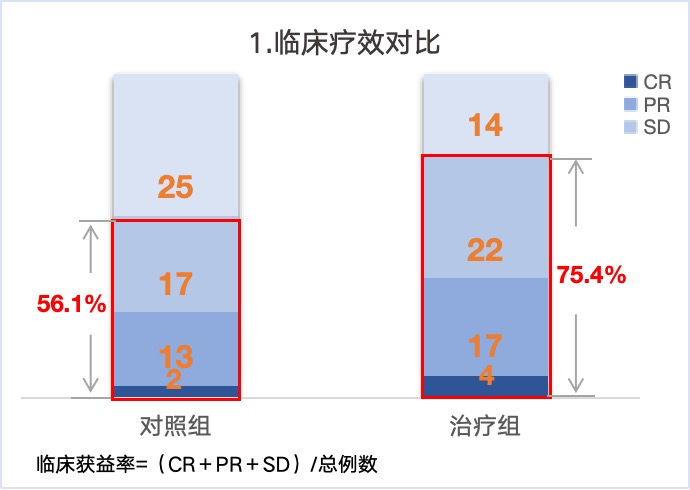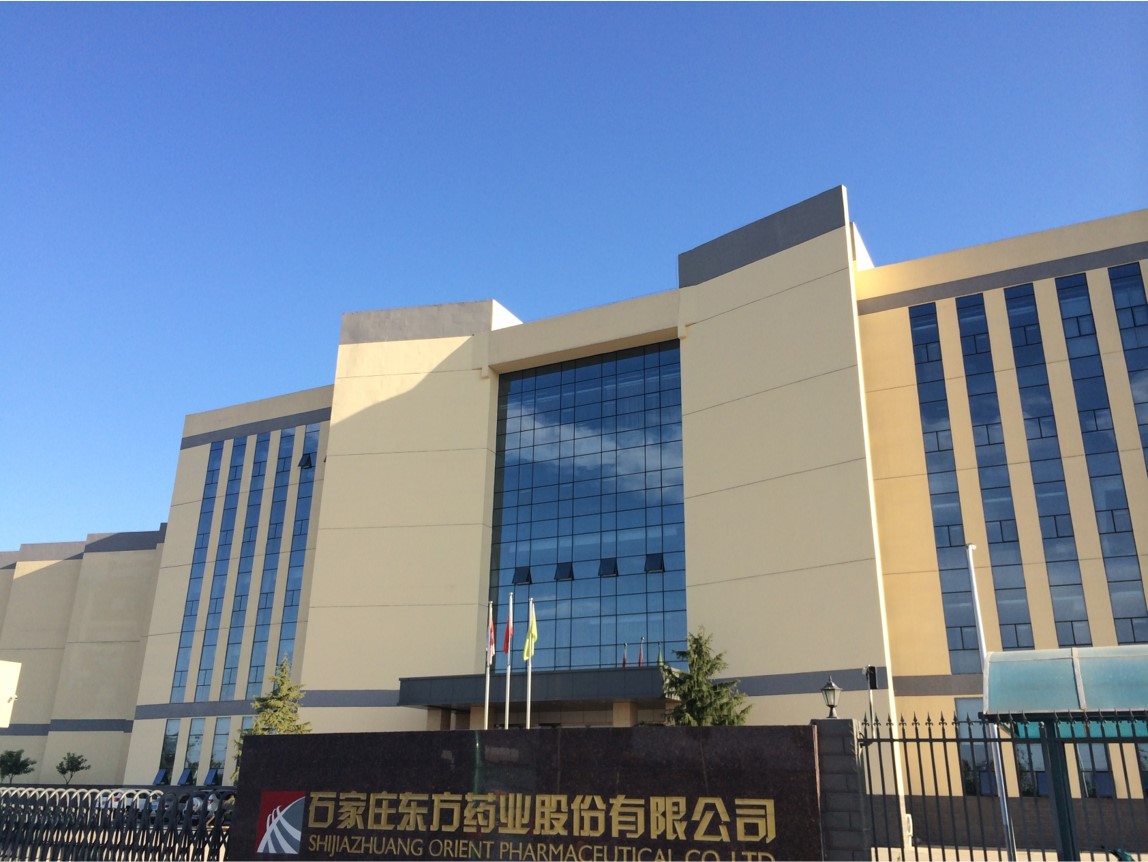巨石阵以北三十公里处,穿过英格兰西南部起伏不平的乡村,是通往新石器时代英国的一扇不太知名的窗户。西肯内特长手推车是由早期的农业社区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建立的,它是一个土丘,有五个小室,上面装饰着巨大的石板。起初,它充当了大约三十二个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的坟墓。但是人们继续参观了1000多年,用像陶器和珠子这样的文物充满了房间,这些文物被解释为是对祖先或神灵的致敬。
这些文物可以使这些访客以及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成为现实。那里的陶器风格的变化有时会回荡欧洲大陆的遥远趋势,例如钟形烧杯的出现,这种联系标志着新思想和新人们在英国的到来。但是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物质的转变形成了一种普遍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沿袭其传统。
人们做事的方式是相同的。都柏林大学的尼尔·卡林说,他们只是使用不同的物质文化“不同的花盆”,他研究爱尔兰和英国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和青铜时代。
但是,去年开始有报道流传,似乎对这种稳定态势提出了挑战。一项研究分析了来自170个古代欧洲人的全基因组数据,其中包括100个与贝尔·贝克烧杯风格的文物有关的数据,该研究表明,建造手推车并将其死者埋葬在那里的人们几乎在公元前2000年就消失了。根据这项研究,新石器时代英国人的遗传血统几乎完全被取代了。然而,新来者以某种方式在许多英国人的传统中继续存在。卡林说,“什么东西不适合我”,他一直在努力使他的研究与DNA发现相协调。
贝尔·贝克烧杯的“重磅炸弹”研究于2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其中包括230多个样本,使其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古代基因组研究。但这只是遗传学对人类过去研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最新例证。自2010年以来,当第一个古代人类基因组被完全测序3时,研究人员已经收集了1300多个个体的数据(请参阅“古代基因组”图),并用它们来绘制农业的兴起,语言的传播和考古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的陶器风格主题的消失。
一些考古学家对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欣喜若狂。古代DNA的工作为他们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激情,他们开始了曾经难以想象的研究,例如对单个墓地中每个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但是其他人则保持谨慎。
考古学家认为古代的DNA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另一半则认为古老的DNA是魔鬼的作品,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斯大学的研究员Philipp Stockhammer讽刺说,他与几年前在德国成立的一家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紧密合作。在学科之间架起桥梁。他说,这项技术并不是万灵药,但考古学家却无视其危险。
但是,一些考古学家担心分子方法已经失去了细微差别。他们对广泛的DNA研究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对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做出了毫无根据,甚至是危险的假设。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马克·范德·林登(Marc Vander Linden)说:“嘿,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整理。”“有点恼人。”?/ p>
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变革性技术。剑桥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在1973年的《文明之前》一书中写道:“当今对史前史的研究处于危机之中”,描述了放射性碳测年的影响。在1940年代和50年代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发这项技术之前,史前学者使用“相对年代学”来确定遗址的年龄。在某些情况下,它依赖于古埃及的日历和对近东思想传播的错误假设。伦弗鲁推测道:“现有教科书中所写的许多史前时代是不足够的:其中的一些,完全是错误的,”。
这不是“轻松的转换” –早期的碳约会工作已经花费了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该技术最终使考古学家不必再花费大部分时间来担心骨头和手工艺品的年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瑞典哥德堡大学研究青铜时代的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认为,这些遗骸的意思是。克里斯蒂安森说:“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自由知识时间开始思考史前社会及其组织方式。”如今,古代DNA提供了同样的机会。克里斯蒂安森已经成为该领域技术领域的最大啦啦队之一。
遗传学和考古学一直困扰着人们30多年了。1985年,第一篇古代人类DNA论文4报道了埃及木乃伊的序列(现在被认为是污染的)。但是在2000年代中后期,测序技术的进步使这些领域陷入了冲突。
2010年,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埃斯克·威勒斯列夫(Eske Willerslev)领导的科学家利用了4000年历史的格陵兰人的一束头发中的DNA来产生了古代人类基因组的第一个完整序列3。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sen)亲眼目睹了这个领域的未来,请威勒斯列夫(Willerslev)合作获得著名的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这将使他们能够研究人类的流动性,因为新石器时代已晚于4,000到000年前的青铜时代。 。
关联问题
迁移一直是考古学家紧张的主要根源。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人类运动是否是考古记录中文化变化的原因,例如贝尔·贝克烧杯现象,还是仅仅是观念在文化交流中传播。通过与它们相关联的文物识别出的人口被视为科学殖民时期的残余,并施加了人工分类。“锅是锅,而不是人”是一种普遍的说法。
此后,大多数考古学家抛弃了这样的观点,即史前史就像一场冒险游戏,在这场冒险中,同质的文化团体在世界地图上征服了自己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人员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了解少数古代遗址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考古学家汤姆·布斯(Tom Booth)说:“考古学已经摆脱了这些宏大的叙述。”他是一个团队的一部分,该团队使用古代DNA来追踪英国农业的到来。“许多人认为您需要了解区域变化才能了解人们的生活。”?/ p>
古老的DNA研究一再证明,一个地区的现代居民通常与过去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口有所不同,无论好坏,这都使人们重新回到了迁移到人类史前时代的广泛关注上。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人口遗传学家戴维·赖希(David Reich)说:“遗传学特别擅长检测种群的变化。”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sen)说,考古学家“准备接受个人旅行过”。但是在他所研究的青铜时代,“嘿,他们并没有为大规模移民做准备。那是新东西。
克里斯蒂安森说,对牙齿中锶同位素5的研究随当地地球化学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一些青铜器时代的人们一生中已经移动了数百公里。他和威勒斯列夫(Willerslev)想知道在此期间,DNA分析是否可以检测整个人群的运动。
他们会竞争。2012年,纽约奥尼昂塔哈特威克学院的考古学家戴维·安东尼(David Anthony)将他和他的同事从俄罗斯萨马拉(Samara)市附近的草原上挖出的人类遗骸装载到车上,其中包括与青铜时代牧民有关的骨头文化称为Yamnaya。他将它们带到Reich在波士顿刚刚建立的古代DNA实验室。像克里斯蒂安森一样,安东尼大胆地对过去进行理论分析。他在2007年的著作《马,轮和语言》中提出,欧亚草原已经成为马驯化和轮式运输现代发展的大熔炉,推动了一种名为“印欧语”的语言在整个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传播。 。
在2015年《自然》论文6,7的决斗中,研究小组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来自当今俄罗斯和乌克兰草原草原的牧民涌入–与亚姆纳亚人文物和坑葬土丘之类的做法有关–取代了很多大约在4,500,000年前的中欧和西欧基因库中。这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墓葬风格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消失以及有线软件的文物的出现相吻合,这些文物分布在整个北欧和中欧。克里斯蒂安森说:“这些结果震惊了考古界。”
剪线钳
这些结论立即遭到了推后。Reich说,其中一些甚至在论文发表之前就开始了。当他在数十位合作者中分发草稿时,几位考古学家退出了该项目。在许多人看来,与有线用品有关的人们已经取代了西欧的新石器时代的组织的想法,令人回想起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 Kossinna)的想法,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 Kossinna)曾将有线用品的文化与现代德国人民联系起来并得到了提倡。称为“定居考古学”的史前“风险板”视图。这个想法后来被纳粹思想所接受。
赖希(Reich)在论文141页的补充材料7中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拒绝了科辛纳的观点,从而赢得了他的合著者。他说,这一集令人大开眼界,它显示了更广泛的受众如何看待声称大规模古代迁徙的基因研究。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在一篇题为“奥斯辛娜微笑”的论文中?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考古学家沃尔克·海德(Volker Heyd)持不同意见,并不是得出人们从草原向西迁移的结论,而是他们的遗传特征如何与复杂的文化表现相融合。他说,有线商品和Yamnaya墓葬的区别在于相似之处,而且至少在俄罗斯草原和早于Yamnaya文化的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据。他认为,这些事实都不能否定遗传学论文的结论,但它们强调了文章在解决考古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方面的不足。在发出武器呼吁之前,海德写道:“虽然我毫无疑问,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没有反映过去的复杂性。”“而不是让遗传学家确定议程并设定信息,我们应该向他们传授过去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p>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南部卫理公会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史前学家安·霍斯堡(Ann Horsburgh)将这种紧张关系归因于沟通问题。考古学和遗传学讲的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但经常使用类似的术语,例如物质文化的名称。她说:“再也没有下雪了。”她指的是英国科学家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化”演讲,哀叹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深刻知识鸿沟。霍斯堡(Horsburgh)抱怨说,遗传结果往往比考古学和人类学对过去的推断优先,而且这种“分子沙文主义”阻止了有意义的交往9。“好像遗传数据是由于人们穿着白大褂而产生的,它们具有关于宇宙的某种非合金真相。” / p>
看到自己的非洲史前领域的霍尔斯堡开始感受到古代基因组学的震撼,她说,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被误解感到沮丧,应该对考古遗体施加影响,要求与遗传学家建立更公平的伙伴关系。“合作并不意味着我给您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您好,您真骨头。”她说:“我给你送一张自然杂志。”那不是合作。
许多考古学家还试图理解遗传学中不便之处。例如,卡林(Carlin)说,贝尔·贝克(Bell Beaker)基因组研究使他踏上了“反思之旅”,在那次活动中,他对自己对过去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仔细研究了研究中包括的DNA样品的选择,以及得出结论的依据,即贝尔·贝克烧杯的出现与英国基因库中90%以上的替代物吻合。卡林说:“不想从一个无知的立场来质疑它。”
像海德(Heyd)一样,他也接受祖先发生了转变(尽管他对其时间和规模有疑问)。实际上,这些结果使他想知道,面对这样的动荡,诸如在西肯尼特长手推车上留下陶器和其他贡品的文化习俗如何持续存在。“泪将这些论文中的很多描述为”描述。他们正在研究遗传标记的运动,但是就这种现象发生的方式或原因而言,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探索,卡林说,他不再受到这种分离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考古学和古老的DNA在讲不同的故事。”他研究的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变化可能与Reich和他的团队正在发现的人口变化相吻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定要。这样的生物学见解将永远无法完全解释考古记录中记录的人类经验。
赖希(Reich)同意他的领域处于“制图阶段”?而遗传学只是勾勒出过去的大致轮廓。广泛的结论(例如2015年草原移民论文中提出的结论)将被更细微的区域性研究取代。
这已经开始发生。尽管贝尔·贝克(Bell Beaker)研究发现英国的基因组成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但它拒绝了文化现象与单个人口有关的观点。在伊比利亚(Iberia),被贝尔·贝克(Bell Beaker)物品埋葬的人与当地早期居民紧密相关,并且与北欧与贝克(Beam)相关的个人(与亚姆纳亚人(Yamnaya)等草原群体有关联)的血统几乎没有渊源。锅是动人的,而不是人。
Reich将他的角色描述为“ of妇”的角色,向考古学家提供了古老的DNA技术,考古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应用它。他预测,“机械学家将接受这项技术,而不会成为Luddite的人,”他们将自己创造。 / p>
强大的伙伴关系
耶拿(Jena)坐落在前东德图林根(Thuringia)州一个昏暗的山谷中,耶拿(Jena)市已成为不太可能成为考古学和遗传学融合的中心。2014年,享有盛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在那建立了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并在古代DNA研究中树立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约翰内斯·克劳斯(Johannes Krause)担任主任。克劳斯(Krause)是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Svante P盲盲bo的子孙。在那里,克劳斯(Krause)研究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10,并帮助发现了一个新的古老人类群体,即Denisovans11。
P盲盲人Bo致力于将遗传学应用于有关古代人类及其亲戚的生物学问题,而Krause则看到了该技术的广阔领域。在领导耶拿研究所之前,他的团队从十四世纪死于黑死病的人的牙齿中识别出了引起鼠疫的细菌的DNA,这是导致大流行的潜在直接原因的第一个直接证据。在耶拿(Kena),克劳斯(Krause)希望不仅在诸如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样的“历史”时期带来遗传学,在考古学中,考古学方法是重建过去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在最近的时期。与历史学家的外联活动仍在进行中,但是考古学和遗传学已完全嵌入该研究所。克劳斯所领导的部门甚至被称为考古学。他说,“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遗传学家正在解决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问题和时期。
克劳斯(Krause)和他的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古代基因组学的制图阶段(他与赖希(Reich)团队紧密合作,开展了许多此类项目。但是去年年底发表的一项研究13专注于德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赢得了考古学家的赞誉,他们一直怀疑大规模的古代DNA研究。
在斯托克哈默(Stockhammer)的带领下,该团队还曾在耶拿研究所(Jena Institute)任职。该小组分析了巴伐利亚南部列奇河谷(Bavarian Lech River Valley)南部的84个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骨骼,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至1700年。在此期间,由母亲遗传的称为线粒体的细胞结构的基因组多样性在上升,这表明大量女性涌入。同时,在儿童时期设定的牙齿中锶同位素水平建议大多数女性都不在当地。在一个案例中,发现彼此生活了几代人的两个相关个人被埋葬了不同的物质文化。换句话说,考古记录中的某些文化变化可能不是由于大规模迁徙,而是由于个别妇女的系统流动造成的。
考古学家们对古老的DNA垂涎三尺,正是这类研究的前景。Stockhammer说,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家将能够在墓地对所有个体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建立当地的家谱,同时还能确定个体如何适应更大的祖先模式。这应该使研究人员能够质疑生物亲缘关系如何与物质文化或地位的继承相关。这些是历史上的大问题。Stockhammer说,现在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方法的另一瞥出现在2月的bioRxiv预印服务器上。本文探讨了欧洲移民时期,当时“蛮族”填补了罗马帝国陷落后留下的空白。在这篇论文中,由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团队用来自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两个中世纪公墓的63个人的家谱与一个名为Longobards的团体建立了联系。他们发现了埋葬在公墓中的高地位外来者的证据:大多数中欧和北欧人的遗传血统与当地人的血统不同,后者往往没有商品就被埋葬,这为某些野蛮人群体包括外来者的想法提供了初步支持。 。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利(Patrick Geary)共同领导了朗巴德(Longobard)研究,他对这项研究未发表评论,因为该研究正在接受同行评审。但是他说,对诸如迁徙时期等历史时期的遗传学研究也有一些陷阱。Geary说,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诸如古气候记录之类的数据纳入他们的工作,并且对古代DNA也会如此。但是他们与考古学家一样,害怕将生物学和文化混为一谈,而有问题的名称,例如弗兰克斯(Franks),哥德(Goths)或维京人(Vikings),将通过基因图谱加以修饰,从而超越了对古代人的看法。他说:“在过去的日子里,历史学家想知道的是身份。”“信奉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 p>
赖希(Reich)承认,他的领域从来没有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希望的那样以细微差别或准确性来处理过去。但是他希望他们最终会被他的领域带来的见识所左右。赖希说:“对人类过去的研究迟到的野蛮人。”“忽视野蛮人是危险的。” / p>
自然555,573-576(2018)
 健康教育网
健康教育网